作者简介

宫楠,男,副教授,华东政法大学法学博士,法学博士后,硕士生导师。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研究院副院长,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黑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俄罗斯问题研究院院长,中俄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数字法治研究院副院长,东北亚法律查明中心副主任。担任中国法学会比较法协会理事,中国法学会民事诉讼法协会理事,黑龙江省法学会俄罗斯法制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客座教授,俄罗斯东北联邦大学客座教授,俄罗斯“瓦尔代俱乐部”专家,华东政法大学数字法学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省级法律咨询专家,CCRC-DCO数据合规官认证。
内容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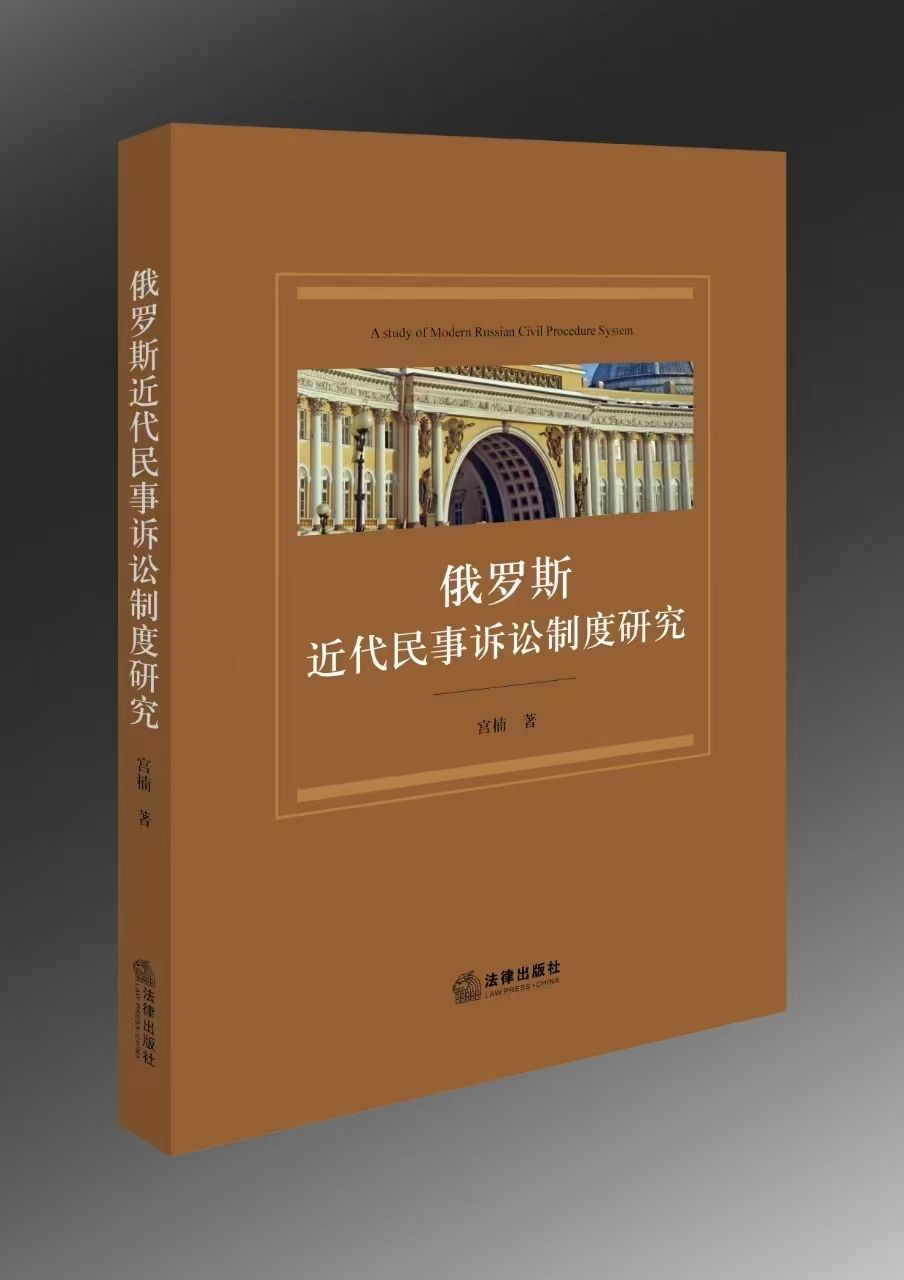
本书撰写源自陈刚教授所提出的法系意识论,并将此种研究方法贯穿全书。学说及制度之创新性发展,非秉承历史成果而不可为,然若置历史积淀于不顾,其结果或是“创新”沦于自言自语,或是“新举措”“新制度”于实务上昙花一现。因此,倘若承继历史成果以前行,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则难脱法系意识之佑启。我国民事诉讼法制现代化的过程,深受苏联法的影响。苏联民事诉讼法保有沙俄时期《民事诉讼条例》之“遗风”,而这部条例又以法国法为主干写成。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外国法的移入,外国民事诉讼法理也相伴而来,我国民事诉讼法学之基本落于德日法学、苏联法学、法国法学之上,兼具美国法理。虽然学理上通常将德日法、苏联法、法国法划归大陆法系,立于美国法之另端,但德日民事诉讼法与苏联及法国的民事诉讼法之间差别甚大,法理上也不直达。因此,未来我国民事制度如何改革及前行,苏联法及俄国法研究乃不可逾越之前提,此乃法系意识使然,也承载着澄清我国民事诉讼理论渊薮,纠正理论误区之重任。
法谚有云,制度是历史的产物,任何司法制度的确立都需要民族内生发展动力,法律发展从传统走向近代化乃至现代化的历史起点、过程、条件以及主体选择是各不相同的,因而法制演进进程中不能不打上特定民族或国度的印记,从而具有特定发展过程的诸多具体历史个性,法律发展的国际化与法律发展的本土化,乃是同一个过程不可分割的两个侧面。本书通过审视俄罗斯近代民事诉讼制度的历史嬗变和发展,通过对俄罗斯古代司法体制的传统形态、近代诉讼法制发展与改造及其基因性品格对现代诉讼法治建设的影响加以论述和分析,力求形成一个较为全面的论证体系,试图重新认识一个民族的法律传统、法律思维以及风俗习惯对于本民族法律演进的影响,了解司法体制改革的困难性与复杂性,反映出因应时代完善诉讼法制而作出不同路径选择的客观规律。
应该说,对于俄罗斯民事诉讼制度现代化和转型研究,国内外学界已经形成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但是对于俄罗斯法治的关注,如果仅仅囿于紧随立法的步伐,那么就会陷入“亦步亦趋”却总是“雾里观花”的视觉盲区,亦会对俄罗斯未来法治之走向,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其原因就在于忽视了对俄罗斯社会法律传统和民众法律意识维度的探究,未将现代俄罗斯法治变革放至历史的维度去全面审视。鉴于此,有必要全面系统地探讨俄罗斯近代民事诉讼制度的形成及其历史意义,揭示其演进特征、内在规律性以及对他国诉讼法制建设的影响,系统考察现代俄罗斯民事司法改革中承袭自1864年《民事诉讼条例》中的传统制度基因,以期通过对俄国传统法制基因的解析以及制度创新的审视,汲取俄罗斯民事司法体系和制度历史嬗变中的规律和方法,对我国正在进行的司法改革有一个理性而深刻的认识。
俄国民事诉讼法制近代化构成了俄罗斯民族国家法治进程中诉讼传统与现代法治建设的纽带,发挥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对其认知需要从历史性、系统性和科学性的维度进行整体把握。对其研究不仅涉及各时期法典中所记载的条文,也包含对整个俄罗斯不同历史时期社会背景、传统文化、法律移植和司法改革的多方位理解和分析。传统上,俄罗斯诉讼法史将十月革命前的民事诉讼制度发展分为三个时期,其以彼得一世改革为近代化发端,以1864年司法改革为契机,尤其是以亚历山大二世颁布的富有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色彩的1864年《民事诉讼条例》为标志,其创制旨在消除旧有司法体制的弊端,疏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形成过程中的民事流转渠道,实现向辩论式诉讼模式的转化,确立新的诉讼原则体系,革新证据制度和证明标准,建立治安法官制度,改革简易程序和上诉程序等具有现代性和科学性的司法制度。应该说,这场肇始于19世纪中叶的司法改革,真正使俄国民事诉讼法制走向成熟,并对现代俄罗斯民事诉讼制度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申言之,1864年亚历山大二世所颁布的《民事诉讼条例》,堪为现代俄罗斯诉讼观念、原则和理论转型的内在立法理念与法治精神之蓝本。俄罗斯近代司法改革塑造的自由主义基因性品格,犹如承载了斯拉夫民主法制文明密码的遗传物质,哪怕我们仅仅从历史长河中截取俄国民事诉讼演进的一个片段,亦可以发现其蕴含的旺盛生命力,能够穿透时空并在钢筋混凝土般的集权主义禁锢下发芽生长,并历次于被“反改革”所扑灭的灰烬中涅槃重生,它克服了法律虚无主义和法律否定主义,建构了俄国民族国家的社会机体,启发了民智和法治意识,法庭不再是沙皇统治权力的延伸,而成为公民制度的学校。
现在,1864年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司法改革经验不仅作为俄罗斯宝贵的法治文明遗产,它穿越时空,也成为重新凝聚独联体国家民族传统和共同信念的一面旗帜。应该说,这有着其深刻的政治历史原因,尤其是在苏联解体各成员国纷纷抛弃原有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时代背景下,而这次曾被誉为19世纪最为成功并对苏联地区国家产生过巨大影响的1864年司法改革,在沙皇集权时代帮助实现了行政权与司法权的相对分离,并通过法官终身任职、审判公开、陪审团审判、律师参与等制度的确立,帮助专制沙皇俄国建立起以欧洲模式为基础的司法体制。可以说,新司法体系的建立为沙皇俄国法治国家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树立了沙皇俄国版图内现代独联体国家民族法律传统的历史连接点,进而形成法律感情上的彼此认同,这也成为服务于后苏联时代区域法律体系一体化以及“大欧亚”战略的重要依托。
俄国诉讼法制近代化进程是对民主法制传统的扬弃和对外国优秀法制经验的借鉴与本土化过程,体现出传统与创新不断融合的特质。若以法系意识方法审视俄罗斯民事诉讼近(现)代化进程,便可发现从《苏俄民事诉讼法典》创制伊始,便已承继《民事诉讼条例》之“遗风”,该部条例主干又师承于1806年《法国民事诉讼法典》。苏联解体以后,英美法渗入色彩日浓,俄罗斯基于《苏俄民事诉讼法典》和1864年《民事诉讼条例》,并辅以西方国家现代立法理念和本国法律传统与法律意识,构建出本国现代民事诉讼法制和理论体系。由此,可以认为俄罗斯民事诉讼法制具有混合法制之特质,而大陆法仍为其基本色调,英美法虽以制度移植影响了其诉讼构造,但未改变其法系意识之源流。
曾经对中国民事诉讼法制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苏维埃民事诉讼法及诉讼理论,若追溯其本源,《民事诉讼条例》中的很多诉讼原则和诉讼制度被苏维埃民事诉讼立法承继下来并加以改造,如法官独立审判原则、直接言词原则、内心确信原则、不间断审理原则、辩论原则、公开原则、陪审员制度、检察长参与民事诉讼、简易程序等。这些原则和制度的影响渗透至苏维埃法律体系中,并通过借鉴与移植,影响到我国法治建设。中国与俄罗斯民事诉讼历史发展具有同构性,加之转型期共同面对的法律现实和社会问题,使得中俄在诉讼原则体系确立、再审功能重塑、便于民众接近司法、应对民事案件激增等问题上,形成了极强的相互借鉴模式。这也就意味着对俄罗斯近代司法改革中改革理念、制度改造、法治建设的分析、解读和反思,对我国进一步拓展司法改革的思路具有重要意义,这亦符合我国的法系传统。
总之,只有深入近代俄罗斯民事诉讼制度具体生成的历史背景及其演进的过程,才能真正认识俄罗斯近代民事司法改革的历史价值和深远影响,并由此预测未来俄罗斯民事诉讼的发展方向。论及现代俄罗斯司法制度之起源,必将溯及俄罗斯1864年《民事诉讼条例》与1923年《苏俄民事诉讼法典》,特别是十月革命前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司法改革经验,这些经验被俄罗斯法学界视为宝贵的民族法律传统,在现代再次成为解决俄罗斯深刻社会问题、保障其政体真正确立的最有力工具,尤其是当俄罗斯民事诉讼面临着从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民事诉讼转向的问题时,再次将注意力投向了俄罗斯近代《民事诉讼条例》中宝贵的民族传统法治经验。于是,我们在后苏联时代看到了众多近代司法制度的“涅槃”与“重生”,如治安法院、陪审法院、辩论式诉讼模式、自由心证等。近代和现代的历次俄罗斯司法改革,无论是在对本民族法制经验的扬弃抑或外国优秀法制经验本土化的过程中,在不同的路径选择中,都始终如一地将俄罗斯民事司法改革目标契合于沙皇亚历山大二世1864年司法改革中的训令:“建立一个迅速、公正、仁慈,向所有俄国民众平等开放的司法体系。”“提高司法权的地位,给予其当然之独立地位,以此获得民众之认同、对法律之尊重,而失去此种尊重,国家富足则无法实现。”
俄罗斯近代民事诉讼制度作为斯拉夫法系的典型代表,除具有混合性质外,兼具民族性、融合性和现代性等典型特征。近代俄罗斯民事司法改革中蕴含的1864年“传统法制基因”的破解,可以帮助我们破译现代俄罗斯法治进程的“基因图谱”。对于我们准确理解和把握苏联民事诉讼法理,在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之间找到平衡点,更加合理和科学地完善我国民事诉讼法制,使之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相适应,将不无助益。本书撰写还有很多不足之处,难免挂一漏万,还请各位专家同仁多多批评指正!